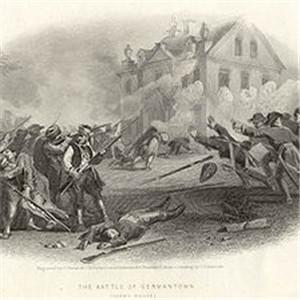日耳曼敦戰(zhàn)役是費城戰(zhàn)役中的一場主要戰(zhàn)斗��。英軍由威廉·何奧帶領(lǐng)�����,大陸軍方面則由華盛頓帶領(lǐng)參戰(zhàn)�。以華盛頓方失敗告終。
日耳曼敦戰(zhàn)役簡介資料
Germantown, Philadelphia
日耳曼敦戰(zhàn)役相關(guān)文獻(xiàn)
日耳曼敦戰(zhàn)役
TheBattleofGermantownwasamajorengagementinthePhiladelphiacampaignoftheAmericanRevolutionaryWar.ItwasfoughtonOctober4,1777,atGermantown,Pennsylvania,betweentheBritishArmyledbySirWilliamHowe,andtheAmericanContinentalArmy,withthe2ndCanadianRegiment,underGeorgeWashington.
日耳曼語族
書寫一些早期(約公元2世紀(jì))的日耳曼語言發(fā)展出自己的盧恩字母(runicalphabet��,北歐文字)��,但這些文字相對來說運用并不廣泛���。東日耳曼語支使用哥特字母����,由烏斐拉主教將圣經(jīng)譯為哥特語時發(fā)展創(chuàng)立�。其后,因為基督教神甫與僧侶既講日耳曼語�,也能夠讀說拉丁語,所以開始用稍加修飾的拉丁字母來書寫日耳曼語言�����。除去標(biāo)準(zhǔn)拉丁字母�,各種日耳曼語言也使用一些標(biāo)音符號和其他字母。其中包括元音變音(umlaut)��、?(Eszett)����、?��、?�、?���、D�����、?和從如尼文中繼承下來的T及?。傳統(tǒng)的印刷體德語經(jīng)常用黑體字��。語言標(biāo)記日耳曼語族一些特征如下:將印歐語系的時態(tài)體系削減為過去時與現(xiàn)在時(或一般時)�。附加齒音后綴(/d/或/t/)來表示過去時態(tài),而不用元音變換(印歐元音變換)���。有兩種動詞變位:規(guī)則變位/弱變位(附加齒音后綴)與不規(guī)則變位/強變位(元音交替)����。英語共有161個不規(guī)則動詞/強動詞�����,都屬于英語本語辭源����。...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zhàn)役
背景英國國會通過《強制法案》后����,美州殖民地與英國政府之間的關(guān)系日益惡化�,其中以波士頓地區(qū)的反抗最為嚴(yán)重。1774年9月���,北美英軍總司令托馬士·蓋奇收繳一座并非屬于反叛者的倉庫火藥���,竟在波士頓外引發(fā)戰(zhàn)爭恐慌,是為火藥危機��。第一次大陸會議恰好在火藥危機后數(shù)日召開�����,會后十二州與會者(佐治亞州未有派員出席)通過決議案���,指斥《強制法案》違反英國憲法���,鼓吹殖民地中止對英貿(mào)易,為馬薩諸塞成立新自治政府����,并聯(lián)署要求英皇喬治三世結(jié)束封鎖波士頓����,修正國會殖民政策�。叛逆者在同年10月于波士頓西郊康科德成立馬薩諸塞州地區(qū)議會,由約翰·漢考克出任議會主席���,成為馬薩諸塞事實上的有效政府�。蓋奇的有效管轄范圍僅限于波士頓一地�����。面對殖民地公然違抗英國權(quán)威���,英國政界的反應(yīng)各有不同。蓋奇因著自身的信念與職責(zé)沖突而搖擺不定���。他在美州已定居超過二十年����,妻子也是于美州成長的殖民者�。身為馬薩諸塞總督�,蓋奇對殖民者爭取自由深感同情��,并未...
日耳曼長城
歷史奧古斯都第一位興建邊墻的羅馬皇帝是奧古斯都����。在9年的條頓堡森林戰(zhàn)役在遭到毀滅性打擊后,他下令建造防御工事�����。一開始是許多分段的短邊墻����,上日耳曼邊墻在萊茵河附近,雷蒂安邊墻在多瑙河附近����。后來,兩段墻連了起來����。克勞狄王朝奧古斯都死后����,羅馬帝國以萊茵河與多瑙河上游作為它的邊界����。擁有法蘭克福的肥沃土地�����,美因茨附近的要塞�����,一直到黑森林的最南端���。由于萊茵河又寬又深��,帝國的北部邊界很穩(wěn)固�,一直保持到帝國衰落�����。南部的情況就不一樣了�����,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很容易被渡過�����,而且這樣長的邊界在防守上很不方便����。在現(xiàn)在的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中部被一塊日耳曼部族的土地嵌入,形成了一個銳角��。在羅馬時期��,這里的日耳曼人還是很稀疏��,許多羅馬臣民從阿爾薩斯-洛林中部跨過數(shù)條河流向東移民�����。當(dāng)韋帕薌(Vespasian)繼承尼祿(Nero)的皇位后�,這個銳角逐漸變鈍。弗拉維王朝薩爾堡附近的邊墻在弗...
原始日耳曼語
原始日耳曼語的演化原始日耳曼語的演化始于這種原始語言因為地域的分隔而使各地的發(fā)音開始分歧���。由于各地的語音習(xí)慣有所不同�����,使聲音慢慢地產(chǎn)生轉(zhuǎn)變��?���?脊艑W(xué)的貢獻(xiàn)基于學(xué)術(shù)界對日耳曼語起源的一種主流觀點,大約在4500年前起��,亦就是北歐青銅時代之前�����,印歐語言的使用者們從日耳曼人的“理論發(fā)源地”(或者直接稱為Urheimat)的中央地區(qū)�,到達(dá)了位于瑞典南部和日德蘭半島(丹麥及德國北部,當(dāng)時的居民稱作朱特人)的廣闊平原地帶����。這里是唯一的一塊沒有發(fā)現(xiàn)前日耳曼語地名的土地。在這些移民未遷入之前此地已然有人居住��,而地名的匱乏或是不完整性勢必意味著原始印歐人曾經(jīng)的長期���、古老而又頻繁的遷入,以至于既有名稱的反復(fù)更替����。如果說從考古學(xué)的角度來看待共同語是一種簡單直接的手段(而不是直截了當(dāng)?shù)丶僭O(shè)),那么印歐語言的使用者的身份就應(yīng)該確認(rèn)為是跨度更為廣泛的繩紋器文化時期(又名條紋陶器文化時期)或戰(zhàn)斧文化時期����,可能還涉及之前一...
日耳曼敦戰(zhàn)役相關(guān)標(biāo)簽